

我的老师
文章字数:3,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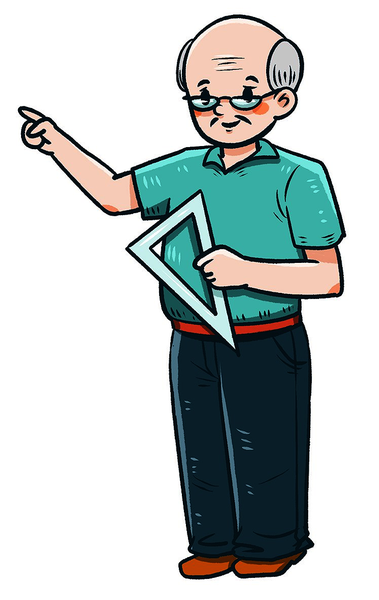
李晓亚
我小学五年,有三年是在村里的小学上的,而这三年都是由一个老师来教的。
说是一所小学,其实就只有一个班,二十几个孩子,年龄还参差不齐,能差一到四岁。那时的农村人,脑子当中根本就没有适龄这个概念,早一年晚一年让孩子上学,基本取决于孩子脑袋“开窍”的时间:孩子闹着去上学了,就送他(她)去学校;孩子傻乎乎地不提上学的事,那就在家中,忙了给父母帮把手,闲了信马由缰地耍去。
说是一所小学,其实教室只有三间平房。据说,平房的主人搬到了县城,于是三间半新不旧的房子就成了了我们的教室。教室的门,是厚重的木头做的,开、关门时就吱吱呀呀地响。窗户是木质的方格子窗户,天冷了,糊张窗户纸;天热了,就揭掉。每当风把窗子上的纸吹得哗哗作响,我就会想起老师教我们唱的《白毛女》的歌词“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说是一个教室,其实教室里的布置极其简单。墙面的正中挂着一块黑板,说是黑板,其实那本来是块白板,是老师让我们从家里各自收集了一些锅灰,趁周末的时候老师自己刷黑的。黑板旁边的窗户下摆着一张桌子,是老师的办公桌,桌子上除了放着几支粉笔,还有木质的教杆,有时放着我们的作业本。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拿起手中神奇的教杆指着黑板上的字让我们念。随着声调的变化,他手中的教杆也像是跳舞似的。有时候他坐在桌前看书,有时候看作业,这时他会戴上老花镜,老花镜戴得很低,压在鼻头上,每当我们在下面有什么动静,他就会把头压低,眼睛上挑,透过镜框的边缘把我们环视一圈,然后轻轻地咳嗽一声。他有时候会拿着一把芭蕉扇,对着我们从前扇到后,从后扇到前。他给我们扇扇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安静,或者会特别大声地读书,那种凉凉的风是从外而内吹拂的,而那暖暖的爱是由内而外升腾的。每当这时,整个教室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课桌是连体的,全都放在用砖头垒起的柱墩儿上,摇摇晃晃的。板凳是自己带的,各式各样的都有。记得我们特别喜欢有靠背的那种小椅子,感觉有种自带光芒的神气。课余时间,我们就把板凳搬到外面“开火车”,我的老师,有时候也会乘坐我们的火车,要么当车头,要么在车尾。
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并没有围墙,四通八达。教室外是一个大院子,院子的西南角是女生厕所,院子的西北角是男生厕所,到了小学三年级时,女生们逐渐发现女生厕所是避难所,男生们拿着虫子一类东西吓我们时,我们就会躲在里面避难。男生一般也不怎么欺负女生,老师常常说,你们二十几个人是兄弟姐妹,大的要让着小的,男孩子要保护女孩子,男孩子欺负女孩子是很丢人的。所以,即使男孩子们拿着虫子吓女生的时候也绝无恶意,他们只是看我们胆小,好玩。其实,我们对毛虫一类的东西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害怕,那样的年龄里,女生大概都会滋生出一种人为创造的脆弱来,看上去像真的需要保护一样。
说是一所学校,其实没有多少教学道具。教室内没有表,教室外面的那棵大杨树上也没有像生产队里那样的大钟,但我的老师手腕上带着一块表,他常常将他的左胳膊一抬,低下头看表,然后吹起口中的小铁哨,哨声就是我们的时间,老师就是时间的主人。
说是一座小学,其实就他一个教师,从早到晚所有的科目都是他上。成为我们的老师时,他60多岁,方脸,头发花白,头顶发量稀少。他表情柔和,但目光坚毅。他脸上常常挂着慈祥的微笑,他一笑,眼睛就眯了起来,连皱纹都在笑,我对老人慈祥形象的定格就是从他开始的。他身材高大挺拔,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这是他多年部队生活保留下来的习惯。每当我有板有眼地把他在体育课上教我们的站军姿、走正步、喊口号、唱军歌、打拍子、拉歌等展现给亲朋好友时,他们都开玩笑似地对我说,一学期五块钱的学费,交得值。他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德高望重,又是县实验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村里人还是希望他能多教一年,再多教一年。他总是说:“老了,教不动喽!”
他的太阳穴附近有块疤,乒乓球大小,我为什么不说鸡蛋大小呢?因为那块伤疤不是椭圆形的,而是圆溜溜地镶嵌在他的太阳穴一边。据说这伤疤是他参加抗日战争的见证,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敢拿他的这块疤开玩笑,那个时候,诸如敬畏、崇拜、英雄、硬汉这些词已在我们心中悄悄萌芽,他在我们心中就是大英雄。
他写一手好字,大半个村子过年时贴的对联,都是出自他之手。他写毛笔字的样子非常专注,非常潇洒,甚至非常帅,我常常一边看他写字,一边观察他写字的神情,不知不觉就伸出指头来自己比划。每次书法课,他都要表扬我,举起我写的字给全班的小朋友展览,我在小朋友的赞美声中获得一种极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毛笔字曾经被拿到县里展览过。我的老爷爷曾经当着我们整个大家族成员的面炫耀过我的毛笔字,他的这一做法几乎扭转了我们整个家族重男轻女的观念。我儿时的自信和精神的丰满几乎达到了人生顶峰。这些年来,每当我回忆童年时,他就会渐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最后又渐渐地模糊。
每周一节的故事课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他给我们讲故事时,既不激情澎湃,也不手舞足蹈,就那么静静地讲,淡淡地讲,我们就静静地听,入神地听。通常课堂上都是他先给我们讲故事,然后又让小朋友讲故事,我和李勇曾经被评为班里的“故事大王”。那时我爱说爱笑,爱讲故事,爱用夸张的语气和夸张的表情以及加重的字音来表达我对故事的理解。他每次见我父母时都会跟我的父母说:“这丫头聪明伶俐,故事讲得全班同学都爱听。”
每周一节的音乐课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他给我们唱得最多的就是军歌,对了,他还给我们唱过《白毛女》,当时我们听得眼泪汪汪的。他给我们唱歌时边唱边指挥,我们跟着边唱边打拍子。通常课堂上都是他先给我们唱歌,然后又让小朋友唱歌,我和丽娟还被评为班里的“唱歌大王”,我曾经教全班同学唱《小草》,好像还领唱过《我的祖国》,是跟收音机上的小喇叭节目学会的。
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他很吝啬,原因是他把粉笔用到最后有黄豆那么大也舍不得扔。但当我偶然听说他妈妈的故事之后,我就再不敢说他吝啬了。故事是这样的:女人好几天没有进食了,渴了、饿了都只能喝水,她肚子里快没有一粒粮食了。就在她快要饿死的时候,她的男人给她带来了一块豆饼,她就那样干啃了吃,男人说,你慢点吃,慢点吃,不要吃得太饱。可是她实在太饿了,她就想能吃顿饱的,吃完豆饼,干渴,喝水,豆饼和水在肚子里发酵了,肚子越胀越大,那个时期的人,肠胃里没有一点油水,肠胃都是薄薄一层,最后竟把胃撑破,死了。
小学三年后,政策有变,几个村里的学校合并为一个大学校,于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搬到了新校,他也再次“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新校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玻璃窗,有独立的高桌子、矮板凳,有办公室,冬天里有炉子,上课有铃声,有分科的教师,却唯独少了他。少了他,一切都不一样了。放学后,我常常和几个伙伴绕着路从他家门口过,到他家门口常常歪着脑袋看他在不在,看见我们时,他就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玩。他说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是明天,是未来,是希望,是未来的科学家、教育家。那时的我们不明白未来和希望在哪里,但我们懵懵懂懂知道,我们担负着人类发展的使命,神圣而又庄严。
初中三年,到镇上去读书,高中三年,到县城去读书,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却经常听我的父母提起他,每次他都不忘问我。高三那年,父母又提到我的老师,母亲说道:你的老师,看起来老了很多,眼也花了,背也驼了,头顶几乎没了头发,言语多了起来,问这问那,问你好不好,等等。元旦前,第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大体是回顾了我们难忘的三年小学生活,说了说高中生活以及对未来的迷茫,还有对以后人生迷迷糊糊的规划。中间还提到,如果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话,就报考一所师范院校。很快,他就给我回了信,信的第一段,我还记得,他写道: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激动,迫不及待地戴上我的老花镜看。第二段,他告诉我要戒“骄”“娇”二字。再一段,他要求我刻苦学习,信中还附有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悬梁锥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故事。在最后一段中,他写道: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记忆力也不好,好多字提起笔来就忘,边查字典边写,七十多了,真是老了。那封信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伴我度过极其难熬的高三阶段。
高三寒假,我去他家里看他,他老了许多,但依旧是和蔼可亲慈祥敦厚,在他家的相框上,别着一张贺年卡,那是我连同信一起寄给他的。
我上大二那年的寒假,得知他患了癌症。我去家里看他,他不在家,去了城市的儿子家里。我开学不久,他便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拒绝住院,拒绝躺在病房的床上,他的儿子带着他把所有的亲朋好友一一看过,做了生命最后的告别。
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便定格在高三那年的暑假。有首歌的歌词这样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长大后,我成了你,却没有机会和你一起分享一名教师的喜怒哀乐。
这就是我的小学,这就是我的老师,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让我怀
念!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 切 的 怀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