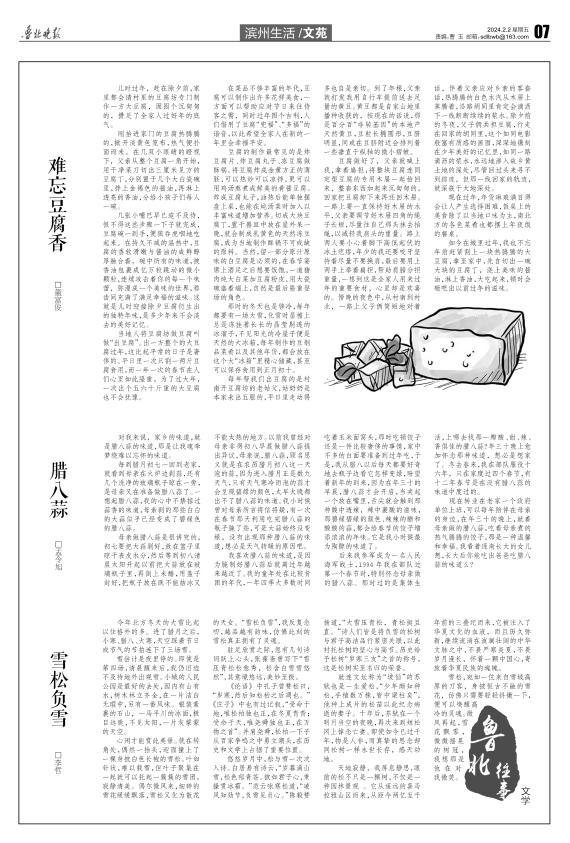难忘豆腐香
文章字数:1,538

董富俊
儿时过年,赶在除夕前,家里都会请村里的豆腐坊专门制作一方大豆腐,囫囵个沉甸甸的,攒足了全家人过好年的底气。
刚抬进家门的豆腐热腾腾的,掀开淡黄色笼布,热气便扑面而来。在几双小眼睛的瞪视下,父亲从整个豆腐一角开始,用干净菜刀切出三厘米见方的豆腐丁,分别置于几个大白瓷碗里,拌上金褐色的酱油,再淋上透亮的香油,分给小孩子们每人一碗。
几张小嘴巴早已迫不及待,恨不得这些步骤一下子就完成,豆腐碗一到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在持久不减的温热中,豆腐的香软滑嫩与酱油的咸鲜醇厚融合着,碗中所有的味道,被香油包裹成亿万粒跳动的微小颗粒,连续攻击着你的每一个味蕾,弥漫成一个美味的世界,唇齿间充满了满足幸福的滋味。这就是儿时迎接除夕豆腐衍生出的独特年味,是多少年来不会淡去的美好记忆。
当地人将豆腐坊做豆腐叫做“出豆腐”。出一方整个的大豆腐过年,这比起平常的日子是奢侈的。平日里一次只割一两斤豆腐食用,而一年一次的春节在人们心里如此隆重,为了过大年,一次出个五六十斤重的大豆腐也不会犹豫。
在菜品不够丰富的年代,豆腐可以制作出许多花样美食,一方面可以帮助应对节日来往待客之需,同时过年图个吉利,人们借用了豆腐“兜福”、“多福”的谐音,以此希望全家人在新的一年里会幸福平安。
豆腐的制作最常见的是炸豆腐片、炸豆腐丸子、冻豆腐做酥锅。将豆腐炸成金黄方正的薄胚,可以热炒可以凉拌,更可以用鸡汤熬煮成鲜美的肴酱豆腐。炸成豆腐丸子,油热后能单独摆盘上桌,也能在炖汤菜时加入以丰富味道增加营养。切成大块豆腐丁,置于器皿中放在屋外呆一晚,就会制成乳黄色的天然冻豆腐,成为当地制作酥锅不可或缺的原料。当然,留一部分原汁原味的白豆腐是必须的,在春节宴席上酒足之后想要饭饱,一道猪肉炖大白菜加豆腐粉皮,用大瓷碗盛着端上,自然是最后隆重登场的角色。
那时的冬天也是够冷,每年都要有一场大雪,化雪时屋檐上总是冻挂着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冰溜子,不见阳光的冷屋子便是天然的大冰箱,每年制作的豆制品菜肴以及其他年货,都会放在这个大“冰箱”里精心储藏,甚至可以保存食用到正月初十。
每年帮我们出豆腐的是村南开豆腐坊的老姑父,姑奶奶是本家未出五服的,平日里走动得多也自是亲切。到了年根,父亲就打发我用自行车提前送去足量的黄豆。黄豆都是自家山地里播种收获的,按现在的话说,那是百分百“非转基因”的本地产天然黄豆,豆粒长椭圆形,豆脐明显,间或在豆脐附近会排列着一些垂直于纵轴的微小褶皱。
豆腐做好了,父亲就喊上我,拿着扁担,将整块豆腐连同定型豆腐的专用木屉一起抬回来,整套东西加起来沉甸甸的,回家把豆腐卸下来再还回木屉。一路上要一直保持好木屉的水平,父亲要调节好木屉四角的绳子长短,尽量往自己那头抹去抬绳,以减轻我肩头的重量。路上两人要小心着脚下高低起伏的冰土疙瘩,年少的我还要咬牙坚持着尽量不要换肩,最后要用上两手上举着扁担,帮助肩膀分担重量,一想到这是全家人用来过年的重要食材,心里却是欢喜的。傍晚的夜色中,从村南到村北,一路上父子俩简短地对着话,伴着父亲应对乡亲的客套话,热腾腾的白色水汽从木屉上蒸腾着,沿路胡同里肯定会滴沥下一线断断续续的浆水。除夕前的冬夜,父子俩共担豆腐,行走在回家的胡同里,这个如同电影般富有质感的画面,深深地镌刻在少年美好的记忆里,如同一路滴沥的浆水,永远地渗入故乡黄土地的深处,尽管回过头来寻不到踪迹,但那一线回家的轨迹,就深嵌于大地深处。
现在过年,年货琳琅满目得会让人产生选择困难,饭桌上的美食除了以当地口味为主,南北方的各色菜肴也都摆上年夜饭的餐桌。
如今在城里过年,我也不忘年前赶紧割上一块热腾腾的大豆腐,拿至家中,先自切出一碗大块的豆腐丁,浇上美味的酱油,淋上香油,大吃起来,顿时会砸吧出以前过年的滋味。